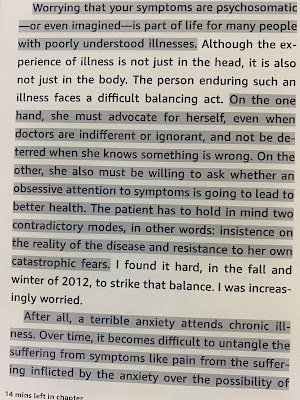据说在中国足有1200种不同的面,每到一个地方,我也很愿意多尝试一下当地的面食,如此简单的原料,竟能演绎出那么多样的品种,不能不让人惊叹。
有时候,这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鄙视链,像我一位四川朋友就觉得江浙一带的面简直寡淡无味,本质上都是一碗阳春面,区别只是浇头不同罢了,远不如川渝的面食滋味浓郁,他尝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尝第二次了。
不论如何,一种面食能在数百年里流传下来,绝对不会是偶然的,那必定是无数人选择的结果,但就像物种一样,现在可能也是这种多样性进入大灭绝的时代。阳春面可能是其中最早消亡的物种之一,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现在面馆里几乎见不到阳春面。清汤寡水的一碗,除了在开水里烫一下,谈不上任何加工,撒点葱花,有时连调料都没有,不仅食客难以下咽,就是店家也卖不出几个钱,对两边都不受欢迎。正因此,现在一般面馆里最低廉的也得是葱油拌面了,但在早些年,阳春面曾是最受穷人欢迎的面食,因为很少有什么食物比它更管饱了。
即便如此,我小时候也很少下面馆,因为不管多便宜,总不如自家煮面更便宜。当然,面还是要买的。崇明岛地处南北之间,水稻、小麦、玉米兼种,但主食毕竟是大米,小麦不过是拿来“交国家粮”,因而乡下说到“打粉”,无一例外都是指糯米粉而非面粉——或许部分也因为江南一带食品工业发展较早,面粉、面条、馄饨皮,从小在我记忆里就都是食品店出售的商品,没听说过哪家自己擀面的。
后来和北方的朋友聊起,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那机器做的,口感肯定不如手工的啊。”那种微妙的口感,对于阳春面而言尤为重要,毕竟它既不像馄饨那样有馅料,也不像别的面点那样有浇头佐料。我从小吃的面条,都是镇上面粉店里机器做的,但近些年来,在全国攻城略地的却是兰州拉面,经过不断揉搓,拉出来的面条在弹性、爽滑、筋道上确实更胜一筹。虽然有些人鼓吹“手工面没必要”,但事实是,如今手工面才是受追捧的面食,就像北方人说的:“兰州拉面你换机器拉一个试试?到山西吃面你要是端出机器做的,估计客人要砸店了!”
最早的面条当然是手工的,面团和好后,搓成拇指粗细的长面条,再掐断水煮;但南宋时因为生活节奏变快,普遍的制面工艺已经不是手捏法,而是轻松便捷的手擀切面法:面团擀成大而薄的面皮,整齐折叠,均匀落刀,面条的大小厚薄一致,还能大幅节省时间。从这一意义上说,拉面是在向传统回归:它不仅费时费力,需要复杂高超的技艺,且几乎不借助什么工具,更不要说机器了。
我小时候在江南乡下的体验全然不同,没有人家会自己和面,面食通常更接近于点心,那是偶尔从面店里买回家来尝个新鲜的,但毕竟不是顿顿都吃。后来读到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惊讶地发现他所描绘的场景,和我所经历的颇为相似:
“我是江南人,自出世以来,脱离母乳,即以稻米为主食,一日三餐,或粥或饭,莫不藉此疗饥。但说到了辅食,每日的点心、间食,一切糕饼之类,都属于麦粉所制。尤其是面条,花样之多,无出其右,有荤面、煎面、冷面、阳春面(价最廉,当时每大碗仅制钱十文,以有阳春十月之语,美其名曰阳春面。今虽已成陈迹而价廉者仍有此称)、糊涂面(此家常食品,以青菜与面条煮得极烂,主妇每煮之以娱老人),种种色色,指不胜屈。”
这种面食的花样,靠的并不是面条自身的筋道,而是各色各样的浇头——时至今日,吴越面馆不论是哪种面点,端上来的通常都是一模一样的一碗阳春面,只不过另搭配一份浇头——或者你愿意的话,两份也可以。这一点,徐路在《杀馋》一文里早就说过,“江南的面条别具一格,与北方大有不同。苏州奥灶、镇江锅盖、淮扬阳春,皆能自成一体,稳稳地面道里占上一席”,但是,“相比起北人吃面讲究的面面筋道,南人更注重面汤和配料,俗称浇头。”
我原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十岁那年,在兰州工作了十五年的父亲回乡。他虽然也是吃米饭长大的,但在西北那么多年,生活习惯中不能不留下第二故乡的痕迹。那时镇上还没有兰州拉面馆,更极少吃牛肉,所以他只能因陋就简,每天早晨捞一碗阳春面,有时是自己下,更多时候则带着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
说实话,这对我而言实属难以下咽。虽然那会儿家里穷,每餐桌上通常都只有一个菜,但好歹有个菜,而阳春面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只吃白饭而无菜下饭,何况多少年里母子相依为命,也没有早餐吃面条的习惯。不管他怎么教育我忆苦思甜,这都无法提振我的食欲。我只是怕浪费受责骂才把一碗光面咽下去,但始终难以理解父亲为什么阳春面吃不腻。
多年后有一次偶然谈起,我才知道,父亲最初到兰州时,也曾很吃不惯,那时本地膳食一多半还都靠各种杂粮,能吃到面条已经算很好,是为了照顾上海来的知青,才在他们每月的口粮中分配一点大米。一个人的胃是最保守的,身为南方人的父亲能在那些年改换胃口,可想是吃了很多碗兰州拉面才拗过来的。
亡友张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都在北京度过,他妻子张霖祖籍山西,老人都特别爱吃面。那时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张霖母亲嘘寒问暖问了许多,未来岳父沉默半晌,一开口就只问了一句:“你爱吃面吗?”他很直率:“不喜欢。”后来张霖说起此事,咯咯直笑:“你知道这一说,是多么伤他老人家的心!”
北方人对面食的那种热爱,可能是我无法真正理解的。黄章晋曾说过,他十三岁之前在新疆长大,之后回到祖籍地,“到了湖南我才发现,我对面食的顽固偏好几乎无法动摇,根本不喜欢各种米制品,甚至觉得米粉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发明。”确实,我遇到过不少北方朋友,哪怕在上海居住了多年,仍然觉得面食才是最好吃的食物。
艰难时世的一种象征
读书多了,我也看到不少记载,证明直到近代,面条在不少地方仍是穷人吃不起的食物。1883年8月3日的《北华捷报》说:“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宽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他高兴地把面条吃一个饱。’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毫无节制地吃面条,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沈艾娣在研究近代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梦醒子》一书里也说:“这是一个以食物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的社会。在下层社会,能不为饮食忧就表明此人已非穷人。在此之上,关键的区别则在于吃的是什么。最穷的人吃最便宜的谷物……过节时,他们才吃面条和肉。”
日本也有阳春面,在战后初期的废墟上,曾帮助许多人挣扎着熬过最艰困的岁月——不过,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那之所以被视为穷人的食物,还不仅因为它没有配料,还在于日本的“阳春面”和中国的不同,不是小麦面粉制成的,而是更廉价的荞麦面。栗良平的名作《一碗阳春面》,原名就是《一碗清汤荞麦面》,那已经不只是一种食物了,还变成了艰难时世中的一种象征。
我也有过。刚毕业那年,薪水微薄,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去公司楼下不远的一家破旧小面馆里吃面,每次点的也几乎都一样:两块五一碗的荷包蛋面——其实就是一碗阳春面加个荷包蛋,店里没有比这更低廉的面食了。
有一次加班了一个通宵,完成了一个艰难的大项目,整个组为之精神一振,我决定下楼去犒劳一下自己,不知怎么的,又踱到那家店里,想了想,叫了一碗大排面。几分钟后,一碗面端到我眼前,又是一碗荷包蛋面。我一怔之下,明白过来:店里的小妹已经认得我了,也知道我每次点的都一样,我又嗓音低沉,她大概根本没听清楚,满以为我点的仍是荷包蛋面。想到这一点,一时心里五味杂陈,也没再要她换大排面了,就此默默把这碗面咽了下去。
对年轻一代来说,不管这样的食物中有什么样的复杂文化感受,可能都太遥远了。在博客时代,专栏作者“王老板”在《不肯说谢谢的人》里有句话让我印象颇深:“由于我是山西人,吃面食长大,而面食这种食品,不管做得多讲究,到嘴巴里都差不多。”
当然,在我看来,这种面和那种面,差别还是不小的。据说在中国足有1200种不同的面,每到一个地方,我也很愿意多尝试一下当地的面食,如此简单的原料,竟能演绎出那么多样的品种,不能不让人惊叹。有时候,这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鄙视链,像我一位四川朋友就觉得江浙一带的面简直寡淡无味,本质上都是一碗阳春面,区别只是浇头不同罢了,远不如川渝的面食滋味浓郁,他尝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想尝第二次了。
我倒并不在意这些,不论如何,一种面食能在数百年里流传下来,绝对不会是偶然的,那必定是无数人选择的结果,但就像物种一样,现在可能也是这种多样性进入大灭绝的时代。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里有这么一句话:“在我看来,将来可能发生的最糟糕事情会是街头食物的消失。街头摊档和墙角小店惯于做面条、馄饨、包子、粥、有馅面团、蒸肉圆、油炸酥点心和数千种其他小吃,在未来新的富裕世界里它们可能受到排挤。”
他是1988年写下这番话的,那是中国社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时候,如今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不能不承认他相当有预见性。那些不同小吃和店铺的消亡,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意味着我们可选择的食物仅剩下少数工业化的产品——就像现在随处可见的料理包。阳春面可能是其中最早消亡的物种之一,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看到instgram上有人給她的狗狗寫的致辭,很感動。小紅書上也同樣有一位博主,對他的蕾拉有著深沉的愛。作爲蕾拉,這狗生也是很值得了了。
Happy 4th Birthday, Mimi! You inspire us everyday with your indefatigable optimism and affection, your steadfastness as an adventurer, and your incessant joie de vivre, swimming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subzero or sweltering.
每一天都是一樣的,沒有是麽進展,所以,慢慢地,要變成周記了。
周一
麗亞帶我去看醫生,終於決定了可以是重新製作一個義肢。媽媽那裏又發物資了。
不管怎麽樣又能訂一陣了。
暴風雨之後有彩虹,而且還是雙彩虹,只是我不能出門去看了。
人的要求其實是可以很卑微的,我現在的願望就是能夠站起來。
周二,周三就是上班,開會,住著雙拐出門轉一圈,然後晚上去
周四
聰帶我出門去做casting。之前,我們去Highland parks的一家新的餐廳。
我們都很喜歡、
我要的sushi burrito,覺得很好吃。這種自由選擇自己想要的ingrediants的小餐館,已經越發流行了。
晚上讓他跟姚剛溝通一下,結果又提我開車的事情。溝通的時候永遠抓不住重點。
周五(5/20/2022)
西游來接我的,一路上雷陣雨。
可能是因爲化療,姚麗娟可憐我,給我發來了Rixi兩張照片。然後跟我講種菜的療愈性。她難道還不能清楚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當然,這些話我沒有對她說,想法太頑固,又不能open-minded,還是算了,不要給自己找麻煩了。
原來還以爲自己能在這一周再接她回來過一周,結果條件不允許。真是想念她。就是不能想,一想呢,四年的洪水就會衝破理智的堤岸。所謂要Manage your emotional。
他可笑地說他在公司吃過東西了,不需要給他準備晚飯了。
到家后,又想摘取義肢,又想在倒胃口之前吃點東西。
燒了一鍋粥。
晚上開始1000篇的拼圖。很喜歡。否則8點不到就像上床睡覺了。不想説話。
英國文學經典。能最快拼出來的都是我曉得的書。
周末
周六一早就醒了。5點,在床上賴到7點才睡。起床後做了運動,決定今日是不太可能到外面去走路,於是墊上運動的時間就長了點。
前一天晚上用了honey medicine,之上晚上睡覺的時候不疼了。
提醒姚剛不要讓Rixi中暑了。
他說已經仍過球,今天不會出門了。然後發了兩張照片過來,
非常珍貴。
猶豫了半天,還是開車去了一次shoprite,這樣義肢穿上也是派點用場,也聯係了開車。回到家后,搗鼓著做蛋糕,第一次打法蛋白失敗,讓我又要浪費四個鷄蛋。還好,第二次打法蛋白成功了,我感覺是容器的問題。下次還是要用比較深的容器。
晚上給他做了冷麵,葱油拌麵,兩塊魚排,一點點菠菜,一盤毛豆,就夠了。我一點胃口都沒有。
繼續拼圖。快要睡覺之前。家裏的飛蟲一下子非常多。心情煩躁。
睡不着,跟瑾雯打了電話,説説話,反而就睡着了。
一覺睡到早晨7點,還是覺得累。家裏很安靜。半夜醒來上過厠所,問聰是否回家。她已經在回家的路上了。
然後再睡了一個sleeping cycle,起來了,感覺啥都不想做。於是決定給自己放假,就啥都不做。
上午就把餛飩做好,反正晚上吃冷餛飩。然後完成了拼圖。覺得很過癮。
聰今天出門去畫畫,然後去紐約看演出。很擔心她的安全問題。讓她一定要小心。她説今天晚上不回來睡了。
下午就把電腦開開。人昏昏欲睡的,還是做了油麵筋塞肉,完成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