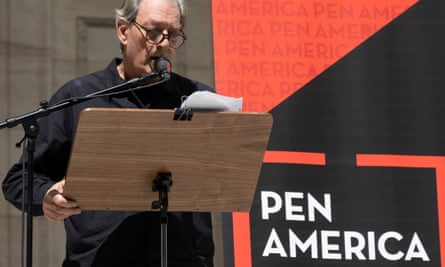本月無事發生,卻又發生了很多事情。小暑大暑都顧不上,因爲整一個月的氣溫就是悶熱,絲毫沒有北方夏日爽氣的熱,也就是溫度雖然高,但是只要在樹蔭之下,縂會感到有意思涼意,前幾年的夏天就是這樣,每次回上海,女兒的濕疹總會復發,并且愈來愈嚴重,回來之後,只要下了飛機,立刻就完全消失,跟空氣的乾燥有一定的關係。而如今,這裏的濕度每天早晨也都是在60-70%之間搖晃,常常讓我想起上海的夏天,粘噠噠的。除了熱,就是瘋狂地降雨,有一天居然收到shelter in place的警報,聼着手機上刺耳的鳴叫聲,一時半會都不知道自己身處與怎樣的一個世界。動不動就flood warning。紐約地鐵站淹水,新澤西22號公路成爲Ocean 22,以至於車行的新車都被雨水冲走。極端天氣似乎都已經成爲了日常。
冒著瓢潑大雨去和高中同學的一家見面。他們從DC北上去波士頓,路過。出門的時候,雨完全就是倒扣的充滿水的浴缸一般,沒有開出兩英里,已經有三輛警車呼嘯而過。心中惦記在外面的女兒,直到收到她平安到家的短信。上次和她們全家見面已經是兩年之前的事情了。時間實在是一條湍急的河流。
本月一個炎熱的夏日清晨,起得早,去河邊,居然碰上了晨霧。其實當天的天氣非常幫忙,氣溫不高,并且沒有毒辣的太陽,應該説是入夏以來難得的舒服的一天。上次和女兒一起進程玩耍還是在疫情之前,很清晰地記得是2019年的馬丁路德金的長周末,去紐約公共圖書館看塞林格的展覽。女兒是他的書迷。而那次參觀後在圖書館買的他的《九故事》,我也是在去年才仔細讀完。物是人非是非常簡練地説明當今的狀況。心中難免有些感慨。
沒有想到這個博物館的特展居然是簡奧斯丁誕辰250周年。五月份的時候看了迷你劇:
Miss Austen,為她們姊妹之間的友誼所感動。展覽中有着她們彼此的通信筆跡,心裏非常感動。本月最後一個周日上午得到了一個姐妹安息主懷的消息,非常震驚。今日參加了她的viewing,見到了很多姐妹。難道真的到了只有婚禮和葬禮才能做到大規模相聚的時候了嘛?
播客
持續地對播客感到倦怠,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似乎都屬於可聽可不聼之間。重聽了魯豫和毛尖的對話,還是喜歡:這個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但是必須直面。
這個月上半個月沉浸在大部頭裏,真正地體會到了read for pleasure。看大部頭還是喜歡紙質書,最好還是Large Print的。以前虛構類的,尤其是長篇很喜歡聼有聲書,畢竟那個時候帶著狗狗可以走很長很長的路,有的時候聽得入了迷,已經走了很長一段時間,就會跟狗狗商量,是否再走一小段?她總是同意的。我至今都還能清晰地記得在哪一段路上聼得書裏的哪一段。就像紙質書,哪一段看得入了迷,會記得是紙張的那個部分,左邊的還是右邊的,書頁的中間還是底部。下半個月,集中閲讀短篇小説集,學習如何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來閲讀,上課,記筆記,為一件事情努力,眼睛很累,但是至少是完成了一件事情。我們要記住我們的done list,不要只專注To Do List。
紙質書:家裏的書架上的,從中國背過來的中文書,這裏買的英文書,還有圖書館借來的。
電子書主要是借不到也買不到的書,大多是中文書。閲讀的媒介微信讀書或者是Kindle。我能感覺自己的集中精力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當然還有有聲書。
虛構之愛:
作者開篇就用一件重大的事情交代了背景,引出故事的主人公諾拉。出於經濟原因,她接受了一份她自己並不中意的工作,并且為自己爭取來了兼職,慢慢地拾起她的生活:開始上唱歌課,買唱片,參加合唱團的選拔賽;她堅持讓自己的兒子回到A班;她去寄宿學校看孩子,咬牙替他做了堅持下來的決定;她女兒的哪有來家裏恰好碰上她給自己買了新裙子;作者真的是非常能描寫細節,無論是行動的還是心裏的:關於Nora在西班牙度假的時候她自己終於能夠一個人睡覺并且睡得那麽深沉;還有面對那麽多的社會關係紛涌而至抑或默然消失的時候的心情。整本書其實都可以覺得是無事發生,但是卻每分每秒都有事發生。托賓的文風非常克制、簡潔,沒有多餘的煽情,但正是這種克制的語言,使得諾拉的情感與內心波動顯得更為真實與深沉。
非虛構之愛:
很薄的一本書,寫了為什麽要去意大利的這座小城市的緣起,仔細觀看了几幅畫的經歷包括和博物館工作人員的一些有限的互動,以及偶遇的來自家鄉的陌生人。作者的語言非常優美,描寫景物和畫面的時候很生動,但是更上一層的是作者本身的思緒,夾雜在看畫中,并不是那麽順利的旅程中,還有被邀請去一個剛認識的陌生人參加家庭聚會中。跟着他的描述,我似乎又回到了這個小城,幻想着自己是否也能有這樣的一段完全和一個陌生小城和喜歡的藝術獨處的時光。
If I stop and think of the people closest to me, of where they might be at this exact moment, what they might be up to, how they might be feeling, what might be preoccupying their thoughts, the weight of their concerns, I become incapable of doing anything else. It is a truly deliberating state. It fills me with immeasurable anxiety, sorrow and long. I haveneverunderstood why the basic fact of the lives of those with whom I am intimate running concurrently and seperately from mine must fill me with such darkness.
Everything we discovered about each other's lives unfolded spontaneously and without suffering the demanding weight of questions... It was not those things that remained with me most vividly but rather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the atmosphere they had crated in their home, the unpretentious authenticity of their curiosities and the kindness of their human feeling. I walked home that evening holding this to my chest as though it were a precious object I had been given.
看了《讀庫2003》裏的那篇“那些最奇怪的大腦”,實在是喜歡,就找來原著。一個周末看完。人的大腦實在是太令人着迷的一個器官了。但是就跟作者裏面提到的“I can scan her brain, but I can't enter her mind。”裏面也稍微提到了真相和假象,難道大多數人都看到的就成了真相嗎?就是事實嗎?還有説到如果身心能夠合拍,那麽在觀察他人,根據環境做決策上就能更勝一籌。我對switching personalities最感興趣,如果真的是因爲大腦生理上的改造就能造就成藝術家的話,那也實在太直接了。
Our reality is merely a controlled halluciation, reined in by our senses.
Becoming unreal and emotional numbness and disconnection with themselves and the outside world, yet all suffer strong feelings of subjective distress over this weirdness.
People who are more in tune with their heartbeat for instance, are better at reading their own emotional feelings. People who are better at interpreting their own feelings are also subsequently better at interpretation the emtions of others. People who have greater interoceptive abilities also make better decisions based on subtle cues in their enviornment, and can make intuitive choices more quickly. They can judge the passing of time more accurately and also perform better in tasks that require them to divided their attention.
本月重讀:
现在的小说可能写不出这本书这样的厚重了。对人性的剖析,对生活的诠释,非常到位。人物刻画非常丰满,故事虽然并不曲折,但也是也有来回荡漾。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6年之後再讀此書,已經物是人非,所以對書中的心理刻畫,人物的塑造和情節的推進有了更深的共鳴。這本書討論了人如何面對自我陰影與選擇道路。它時間跨度很大,把兩個家族的點點滴滴都描述得很細膩,生活殘酷,而偶爾也會被溫柔對待,留下的是對人的尊重與希望。故事有濃厚的《聖經·創世記》中該隱與亞伯的影子,探討兄弟之間的愛與嫉妒、選擇與命運。書的結尾Adam對兒子的回答説出了這本書的中心:「你可以愛,也可以恨;你可以原諒,也可以傷害;你可以選擇。」
其他的閲讀:
讀過作者的另一篇小説,很喜歡,因爲反烏托邦的設定。這本也是一本科幻小説,和上一本書有點類似。多人物敘事的角度給這本書怎加了豐富度,但是也感覺有點一碗水端平的平實感。我也理解作者想借用他們來述説悲傷,喪失,兄弟姐妹之情的複雜性。非常喜歡書中的兩端描述,一是有關罌粟花本身的描述,明確點題,我也漲了一點小知識,想起在古羅馬廣場遺址中看到的映入眼簾的罌粟花,還有在佛羅倫薩一個街邊畫家買的小小一副罌粟花的畫,如此鏈接,感覺人生很奇妙。第二段就是講到那些有傷痛的人也是了不起的人,可能并沒有對人類社會做出了貢獻,但是他/她們也是影響了其他人生活的人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也是特殊的。整個情節略顯有點平淡,如果在展開一點會更加飽滿一些。
用書信的方式編制了一個年老女子的生活,感覺非常直入人心,因爲寫信給人帶來的親密感。一個普通人的一生,有得到,有失去,在晚年還有了一個非常令人愉悅的意外。
看過作者的另外一本寫他的狗狗的書,非常喜歡他的文字,而這一本回憶錄,要比狗狗的那本沉重很多,至少前半本書是的。作者講述了他的童年的掙扎,父親的酗酒非常糟糕地影響着他的媽媽和他們兄弟三個。在接近書的尾聲的時候,他與父親的對話是非常真是的,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父親,這麽刨析自己,是非常非常難等可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就算有,公佈與衆更是難上加難的。看到他獲得了普利策獎并且説服媽媽一起去參加頒獎儀式的時候,我内心為他們開心。榮譽看似就一瞬間,但是要達到那樣的成就,真是一朝一夕地持續的努力,流淌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這個系列的南方回憶錄,我會去看第二本。
很喜歡這個系列,雖然是給青少年看的,是很好的簡潔的人物小傳。
精神絮叨。感覺沉重,像是做了很久的體力活,疲憊,但是好的那種疲憊。
非常藝術小白友好。詼諧幽默的筆調貫穿始終,不知不覺中一本書就看完了。根據作者的指點學着去看畫,很多陰影如果作者不指出,看華的時候并不會注意到,就算注意到了,可能也不會去細想。這個系列非常不錯。講着講着八卦就講了一段藝術史。
好棒的漫畫,有内容有涵義。期待更多的作品。
一個人的想象,只是臆想,我們去順應它,也只能形成一個幻象。但共同想象就不通了,人類的共同想象,本就是創造出不存在的事物,像是金錢啊,功名啊,都是人類想象出來的。我們去順應人類的共同想象,就能得到他們的這種力量,化爲己有,便創造出你我的人身。説到底,修成人身依靠的,并不是妖的能力,而是許許多多對你有所期待,并得到滿足的人類的能力,只要所化之形是足夠滿足衆人之心,每隻妖都可以變成人。
翻出從中國背過來的《讀庫》,最妙的就是隨機抽取,一本裏多少總會有一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對虛構的喜愛應該説都是從《讀庫》培養出來的。
《電流之戰》出乎意料地精彩,讓我想有更加去瞭解那段歷史的願望。文章寫成這樣,我覺得也算是相當成功了。吉井忍的《中國殘留邦人》讓我看得很不是滋味,首先這個題目就感覺不是那麽舒服,這群人是沒有選擇的。聽過故事FM裏有關日本接生婆的那幾集,講述要生動很多。《月上東山》裏的那句“谁不是根据世俗的安排,一步步地走向真实生活,并一天天地变成行走的躯体,对精神世界的渴求变得毫无热望呢?”給了我深深的共鳴。《百年前的成都吃相》把我給看樂了,對於吃,可真是不遺餘力,無論是真正意義上的吃本身,還是記載有關吃的一切。《捂住口鼻和臉蛋》講述的是口罩史,在這期出版的時候,的確應景。其餘的幾篇無感,感覺有點充數。
《不存在的存在》比第一篇也是有關人工智能更加讓人有直觀的感受,所以衝擊力更加强一些。《我和父亲在工地》很接地氣,真情實感流露得非常自然,很好的非虛構作品。李雙雙後面的故事有那麽多沒有想到。其餘幾篇感覺很一般,尤其是考證那一篇,可能作者想從考證書這件事情來反應一個大時代?感覺非常“和我沒有關係。”
第一篇几乎占據了這本書的1/3,是很多老藝術家的訪談,很多有意思的細節。《临城劫车案与“土匪邮票” 》這一篇非常有意思,對這樣在歷史長河的仔細打撈值得讓人琢磨。非常喜歡《公共图书馆那些事儿》,這樣的文章總是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其餘的比較一般。
很失望。因爲一直很喜歡這個作者的其他書籍,從他的Beartown開始,幾乎看過他所有的小説,也去參加過作者的讀者見面會,就跟一個追星的粉絲一樣請作者簽名,拍照留影。所以聽説他會出版新的小説,心中充滿着盼望。只是他來美國做新書宣傳的時候,時間上正好錯開了,沒能趕上。開頭還算吸引人,但是看完之後,確切地說,我堅持讀到了75%左右實在是讀不下去了,就跳到了結尾,感覺真本書就是無數情緒地渲染,就像是水彩畫把顔料倒在紙上,但是實在是看不出畫得是啥。書中還是不時地囘出現作者充滿智慧的句子,但是整本書顯得非常鬆散。我也反問自己,是不是我的問題,跟書中的青少年實在是不能共情?朗讀者還是不錯。我想,也許我已經離開他所寫的世界了。
開頭還行,至少能讓我想讀下去。還不到一半的時候,就有點開始拖泥帶水了,我不能公情男主,感覺作爲一個在監獄的藝術家,實在是有點矯情,而且,寫監獄的場景也沒有啥新意,結尾也是非常草率,感覺最後也還是一個問號。
對這本書還是有着一定的期待的,結果還是很失望。前半段已經非常緩慢了,我忍着聽到了女主去了意大利,我想這個時候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發生了,還是沒有,終於在快要80%整本書的時候,我終於受不了了。對書中的人物,我沒有一個是有好感的,而故事又原地踏步,真是浪費了那麽多時間。不推薦。有聲書的朗讀者還是不錯,意大利口音惟妙惟肖,但是也擋不住一個毫無意思的故事啊。
儘管有聲書的朗讀者是我最喜歡的朗讀者,雖然我讀過這個作者的好幾本書,總體印象還不錯,但是讀了一下我幾個覺得還比較靠譜的讀者的評價,我決定放棄這本書。對浪漫小説無感,要看的書實在太多,要精選!
影視
電影之愛:
一定是在疫情隔離期間找到的這部片子,一直擱置着,似乎總有其他的影片要看。這次從圖書館借來碟片,慢慢地沉浸在這三個小時當中。借來的還包括另一張碟片,是這部影片拍攝的花絮。小人物在大時代裏的命運,看似自己可以做出一定的選擇,比如他轉向普魯士軍隊的時候,比如他突然向應該刺探情報的對象訴説衷腸的時候,比如他向他的妻子表達愛意的時候,比如他鞭打他的繼子的時候,比如他決定想地下開槍而不是瞄準他的機子,但是也正是這樣的一系列決定,生活中的一個個時刻纍計起來,成就了人的一生。影片拍攝得實在太美了,每一幀畫面都如油畫,視角的切換,遠近的推進,還有那睿智的旁白,背景音樂,實在是一部常看常新的影片。
電視劇之愛:
Elsa在整部劇情中的旁白就是一部非常優美的小説敘述。沒有想到這麽一部西進運動是這麽讓人流淚,不停地告別,主動的,被動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永遠在走細小的鋼絲。幾位人物刻畫得非常鮮明,最愛老警探,他已經看透了人生,只想最後帶着他的太太的靈魂一起看看大海。一路上,人的劣性暴露無遺,值得安慰的是,同時也有稀少的溫暖。那是一場殘酷的征程,所以能透出很多人(生)的光(芒)。
一直很喜歡這部劇,就是全片充斥着焦慮:每個人的生活本身似乎就是困境本身。大家都面臨選擇,但是事實是選項並不多,無非就是矮子中間選拔一個高個吧了。我很喜歡Sugar對Bear說的,“我看到了你眼中的spark”,是一個good sadness。我就回想我生活中的good sadness。這樣的組合比較夢幻了,已經傷感了,怎麽還可能是好的。其實生活可能就是這樣吧,處處都是矛盾的混合體。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頭抬出水面,繼續保持這個姿勢,生活。
八年前看的書,這次從圖書館借來DVD,只能一口氣看完。幾個演員都實在是太棒了,已經不太能記得是否和原著細節上有出入。我也不强求從原著改編的就一定要忠實原著了。改變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個新的故事來閲讀/觀看。老金的確是一個太會講故事的作者,故事框架在,想象并且填充細節后,立刻就可以自圓其説。恐怖片恐怖在給你一個上帝視角,讀者/觀衆知道書裏/劇裏的各自角色,只是他們自己並不知道,所以才恐怖。
不遵從原著沒有關係,可以作爲一個全新的電視劇來看。人物塑造得非常不錯,最後的結尾也是意料之中了,他只想意念活著,這樣以來一切對他來説才真正地開始。
非常可惜沒有第四季,因爲這一季的結尾實際上是可以有多種解釋的,而且女兒懷孕這條綫也是可以展開的。還是一如既往地扣人心弦,不過自己覺得口味還是重了一些,那些惡人們,真的是純粹的邪惡,如此癡迷一個作者的作品中,我感到看書對他們來説也跟吸大麻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感覺就是用那些文字達到他們的HIGH。看到“正方”人物們的形象越來越飽滿,再次為沒有第四季而感到可惜。有時間再復習一遍原著。
記錄片最愛:
從圖書館借來的《假面》DVD,沒有想到有兩張碟。這另一張就是這個紀錄片,真是意外的驚喜。主角的敘述非常動人,尤其是日記和最後在小熊裏發現了他給她寫的紙條。
兩個老意大利吃客的煽情回憶錄。拍攝得很不錯,很有代入感。為有這樣的友誼二乾杯吧。能夠如此熱愛美食的人一定也熱愛生活。
其餘影視
這個月集中看了希區柯克的影片,因爲打開Netflix,就一直提醒我,“這些電影這個月就要離開這個平臺了,抓緊時間啊。”所以,我聽勸,抓緊了時間。
標志想看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那個時候是隨心所欲地標記“想看”和“想讀”。最近一連看了好幾部希區柯克導斯圖爾特演的片子,這部實在可稱爲是經典之作。太多的象徵和隱喻在其中,我們都是想控制周身的一切,從物質的到心靈的,只是這永遠會是一個幻像。影片的後半部分讓我感到不適,最終他喜愛的只是他心中的一個形象而已,而她居然也同意了一起扮演布娃娃,不過影片的結尾卻一步步地把懸疑推向高潮,直至最後一秒而嘎然而止。影片中兩個人去看大樹的情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大自然面前,我們人算什麽。感嘆一下那個時代的扮相真的是精緻啊,君子淑女,在快要70年后的今天看,依然動人。
男主在窗前無聊地偷窺正如當今我們在社交媒體上互相關注對方一樣,點贊不走心,只是為了不要FOMO,實在可悲。因爲不大會從這樣的偷窺中發現謀殺案吧。格蕾丝·凯利格蕾丝·凯利實在是美麗,溫柔,賢惠,勇敢,只是最後一個鏡頭讓我有了困惑,想看時尚雜志就放鬆地看唄。
我怎麽覺得從頭至尾都表現了男主的自以爲是和輕率愚蠢。作爲妻子和孩子的媽媽,女主的形象明亮很多,有頭腦,并且付諸行動。尤其是唱歌的時候,真是魅力四射。在劇場的那場戯非常精彩,一時間一切都在發生,結果卻與預料的大相徑庭。也算是非常希區柯克的風格了。
我算是斯图尔特周旋上了,最近一直在看他的影片。這部經典的片子女兒在好幾年前的飛機上看過,就推薦給我。看我標志想看的時間是2019年的聖誕節之後,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都想有點好的消息,而這部被譽爲聖誕節期間最受歡迎的影片卻遲遲沒有機會看。男主比我前兩部看的影片要年輕十歲,但是也真是吵鬧啊,一直到影片的後半段,天使出現之後,影片突然進入了另一種風格,他的人生被完全抹除了,他看到了他不存在的人生是怎樣的,然後珍惜了他現在的困境,最後小鎮上的人們紛涌而至,慷慨解囊,實在是太美好了。
女主勇猛,而且果斷!
完全是衝著演員去看的,的確是妙計。
為什麽這樣的美麗人們只會投以惡意或者加以利用,如果利用不到就摧毀?女主太美麗了。
成人的“頭腦特工隊”,這裏設置還是不錯的。感覺意大利語非常密集,又是一場基本上是靠對話驅動的電影,閃光的點還是蠻多的。比如説"The idea of the family as a container of happiness is overrated"。其中男女主角互相回憶並説出對方穿的衣服那一幕真是太能relate了。很不錯,很久沒有看到一部還看得下去的愛情片了。
幾位演員比較養眼,故事本身還是有點老套,雖然最後結婚的場景是在繁忙的登記處,但是他們在看他人的婚禮的時候說的那段話才是最真實的。而且結尾處强行和Sophie和好有點畫蛇添足。
60多年後觀看這部影片,就是感到以前是瘋子,現在還是瘋子。
開頭真的是很難去理解。有一幕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的就是女主的臉部特寫,光纖漸漸弱下來,直到最後被黑暗吞噬。沒有眼花繚亂的情節,但是卻讓人感到心理上的緊張。如何來理解“不能發出聲音”?是我們不會表達,還是我們就算表達也沒有用?或者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不可能性?
整個故事的框架還是可以的,中間有幾集注水有點多,回憶場景也有點多。對於洪亮這個人物的角色,我有點吃不準,不知道他是故意大智若愚呢還是真的愚蠢得唯唯諾諾,猶豫不決而造成了有些人員不必要的犧牲。真是有點替那些角色着急。有幾處當背景音樂/歌曲放出來的時候,還是感覺鷄皮疙瘩都起來了。這樣的劇情能放出來也是不易,且看且珍惜吧。
《嗜血法医》三季(加入條目就被告知出錯)
看完第一季明白了該劇能上美國電影學會獲獎名單。構思實在是很巧妙,題材也是不多見。變態的殺手很多,反社會人格也很多,變態殺人的故事也很多,翻來復起炒冷飯就沒有啥可以表現的了。演員也很能入戲。配角也很鮮活,也能看得出來有些人設也是有點為寫而寫了。比如他的莫名其妙的女朋友,感覺一直就是他在付出;比如他的妹妹,戀愛閙起來,智商為負。他的隊友倒是還都很有自己的特色。會慢慢追下去,反正夏日正長。
第二季也繼續榮登了美國電影學會獲獎名單。新一季裏一個濃重英國口音的女子闖入劇中,其實的確是他的靈魂伴侶,在黑暗的那一半上。
上一季和這一季都是引進了新人,攪亂了男主的生活,都是黑暗的力量。但是黑暗和黑暗還不一樣,所以人物的發展撐起了整部劇。尤其是他和養父夢境般的談話。男主的妹妹也是,一季一個男朋友。婚禮總是會催人淚下。
過去兩個月,因爲一周一集這部劇,可以有所盼望。女主的性格很不錯,只是最後一集她居然被人欺騙了,當然,結局了嘛,來個能改觀的前設,最後撿小狗還是動人。輕鬆好劇,不費腦子,看她如何解開謎團。
風光大片,所有的元素都包含了:親情,懸疑,槍殺,贖罪,原住民,和美好的風光。
為了妮可·基德曼才點開的,第一季已經很不盡人意了,為什麽我還要繼續看第二季,真是奇怪。幫助和治愈就是迷幻藥嗎?太奇怪了。請不要再有第三季了。
文章
Writing as a deliberative, iterative process involving, drafting, feedback (from peers and also from ChatGPT) and revision. ..Reverting to a pen and paper can feel stifling. In the end, most people would probably rather have a swifter travel than sharper memories.
...implore them to wrestle with difficiulty and abstraction. Society value high-speed takes, not the slow deliber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Educ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humanities, rests on a belief that, alongside the practical things students might retain, some arcane idea mentioned in passing might take root in their mind, blossoming years in the future. It is risk, doubt and failure that make us human.
”The End of the Essay" by Hua Hsu (The New Yorker July 7 2025)
What we stand to lose is not just a skill but a mode of being: the pleasure of invention, the felt life of the mind at work. I am a writer because I know of no art form or technology more capable than the book of expanding my sens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live.
Will the wide-scale adoption of A.I. produce a flatlining of thought, where there was once the electricity of creativity? It is a little bit too easy to imagine that in a world of outsourced fluency, we might end up doing less and less by ourselves, while believing we’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apable.
This sheer human pleasure in inventiveness is what I want my children to hold onto, and what using A.I. threatens to erode.
When I write, the process is full of risk, error and painstaking self-correction. It arrives somewhere surprising only when I’ve stayed in uncertainty long enough to find out what I had initially failed to understand. This attention to the world is worth trying to preserve: The act of care that makes meaning — or insight — possible. To do so will require thought and work.
"I Teach Creative Writing. This Is What A.I. Is Doing to Students". By Meghan O’Rourk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25)